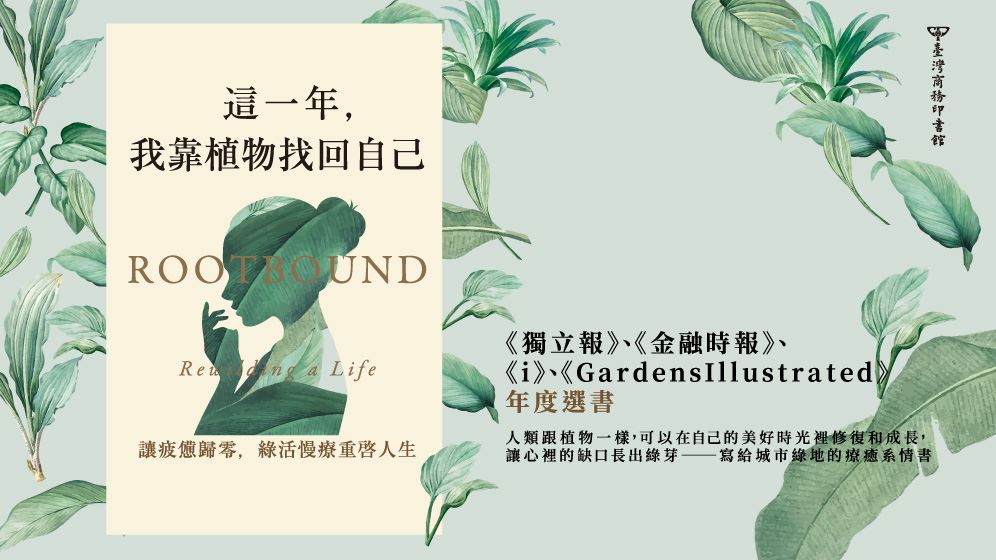文 / 愛麗絲・文森(Alice Vincent)
【精選書摘分享】這一年,我靠植物找回自己——讓疲憊歸零,綠活慢療重啓人生
我的生活已安定下來好些日子。這是我在這個家迎來的第三個夏天,也是我在二十多歲階段,定居於相同地點時間最長的一次。位於山頂的公寓承載著四季的重量,從我住的五樓可望見整座城市,餐桌上就能捕捉到晨昏時刻的光影。冬天時霧氣繚繞,清晨一片朦朧,凝結的水珠從窗面滴淌而下,積聚在窗台上;有時則是暴風雨襲上的雨滴。隨著炎夏到來,我們會打開窗,讓白晝光線傾瀉而入,直到傍晚的彩霞將牆面染成緋紅。有時一陣勁風會吹進長廊,砰地一聲關上一端的門,打斷此處蒼白的寧靜。
陽台是我最喜歡的公寓空間。我喜歡這兒的玲瓏別緻—長度不到四公尺,寬度剛好超過一公尺,兩側都裝著飽經風霜的克里特爾風(Crittall-framed)窗門。陽台的門很小,大夥都得一邊小心翼翼地側身跨過,一邊嚷嚷著自己很可能會被卡住,經常還會緊張地笑起來。不過,我一跨過這扇門,就會突然感受到自由;在這裡我可以看到天空,感覺自己就像是被天空擁抱,得以暢快呼吸。我感覺胸口一鬆,有更多的空間可以吐納出胸中的氣息。
我開始試著多花點時間在陽台。接著我發現,自己待在這個小小的空中窗台的時間越來越長了。我想為這個蕭索的角落注入些許生氣,於是先挑了薄荷、百里香和鼠尾草等香草植物,將它們胡亂塞進從披薩餅店外拾來的常見番茄罐裡。結果才沒幾週,這些可憐的植物就被我澆太多水澆死了。我更養成了個習慣,時常在週日一早帶著二十英鎊紙鈔出門,往東前往哥倫比亞路花市,把中意的植物都塞進手提袋裡,搭火車帶它們回家,然後用自以為對它們好的方式虐待它們。
森寶利(Sainsbury’s)和利多(Lidl)超市所販售的特價植物,也輪番調教著我的園藝技巧。有些植栽被我種死了,有些卻使我大感驚奇。我也是花了好一段時間才知道,澆水前得先用手觸摸表土,好判斷植物是否需要澆水。相反地,我只是一味地把滿滿的關愛,澆灌在它們已然濕透的根部。不然就是放任狂風摧殘嬌嫩的植物。還把植株的生長高度(就算看來疲軟無力)看作自己栽種有方,而非植物渴求光線或養分的表現,而且當植物開了花(為了在過早枯萎前用盡最後一絲能量開花並製造種子),我也任其盡情綻放,只為了滿足我的好奇心和驕傲。有些花開得很美;即便是現在,我也會歡欣地任由芝麻菜開花,因為它們那精緻的風車狀白色花絮是我最喜愛的。我會在花朵凋謝前,將它們從莖上切下來,加到沙拉裡,好好品嚐那帶著些許堅果香氣的新奇滋味。
我在好奇心、小小的成功和徹底失敗的驅使下,放縱地從事園藝活動。我沒本錢實驗,只好開始東挖西撿。我把一盤盤一年生植物(也就是在一年內發芽、開花、結果的植物)移植到一個個搶救來的容器裡:木托盤、從咖哩屋外人行道上撿來的油罐,以及從苗圃裡搜刮來的剩餘塑料盆。到了隔年夏天,我讓香豌豆爬上我做的簡陋棚架,那是用我在公園找到的枯木和麻繩搭建而成。到了第三年春天,我又用同樣的麻繩將一塊鐵絲網固定在公寓磚牆上,好讓那年的植栽攀爬。
我確實期待它們能攀上那面鐵絲網,儘管它們通常沒能達陣。我當時還不了解不同肥料之間的差別、組合盆栽的需求,或者良好養分的益處。我只透過以往錯誤的經驗,以及網路上令人困惑的資訊,來掌握基本知識,例如光照、遮蔭和生長空間。我渴望種植各式植物,透過讓它們持續成長,體會大自然溫柔的束縛:種在小容器裡的莙薘菜無法成長茁壯,但若把一整包芥菜籽撒到小容器裡,並且樂觀地重複堆肥,兩季後就會看到葉子冒出來。
我並未意識到自己的知識如同灰塵般不斷累積,也沒有刻意去測試;就只是日積月累,一天知道得比一天多。我對植物的了解不斷演進、持續,隨著季節遞嬗有所變化,成功時便有所得,失敗時便歸零,但未曾稍減。愈發了解植物,我的熱情愈發高漲。我開始對陽台以及上頭栽種的所有植物充滿渴望。剛迷上園藝的頭幾年,陽台多數時候都並非綠意盎然的模樣,但在這些破爛花盆、器皿和食品罐頭堆裡,還是能瞥見某些存在於自然定律與我的掌控之間的生命。我會留連於陽台門邊,額頭抵著玻璃,靜靜待在那裡;若是天氣冷,呼出的熱氣就會遮蔽眼前的視線。喬許會問我在做什麼,而我總是回答:「只是看看。」
生活與工作時而停滯不前,時而匆匆流逝。我開始依賴觀察天色來感受時間的流動。這間公寓可以飽覽從巴特西區延伸至金絲雀碼頭的景色,在碎片大廈(Shard)的微光中,置身其中的一切都顯得如此渺小。不過,大廈就算再耀眼,也難敵那片景色上空時刻變化的繽紛雲彩。不管是否受到注目,雲層都會逐漸增厚,在無聲的演出中兀自變換著色彩。因此,我學會了在一個個晨昏時刻,觀察太陽在地平線上的軌跡。我待在陽台觀察天空,不自覺花上幾小時嘗試解開大自然的小小謎團。這讓我得以將愈形渺小的自己放進一個大到不真實的系統,一個超出我所能控制的系統。
一切分崩離析的那天早晨,萬里藍天。是那種深邃無比,地面上毫無陰影的藍。我一邊望著天空,一邊漫不經心地舀起麥片送進嘴裡,這時喬許走了過來,告訴我他想分開一陣子;我們彼此都需要分開一陣子。就在幾分鐘前,我才小心翼翼地掙脫他的懷抱離開臥房。這實在太沒道理了。我無法處理,也不想處理。也許當下他曾試圖解釋,但我不記得他說了些什麼;傳進我耳裡的話變得模糊不清,就好像他在水裡說話一樣。碗裡的麥片漸漸軟化,沉入牛奶中。我感覺自己也沉沒了。當我為了呼吸浮上水面,空氣中只剩下一句話:「我覺得我不愛你了。」
六月變得冷冽又潮濕,時間也隨之變得緩慢而沉悶。我發現,他還要不要我,我會不會被拋棄,這種不確定令人難以忍受。儘管我嘗試想解開這個難題,時常在腦海中推演無數種不同的情節,卻發現唯一令人滿意的解答,就是不去承認已成定局的事實。我開始萌生離開英國的念頭,因為我無法在倫敦過著沒有他的日子。正當我凝視那個由曖昧不明的分手所造成的裂縫,並想像可預見的未來——閒置的房間和沙發,沉重的房租,被淚水以及如暴風般在腦中肆虐咆哮的遺憾與孤獨所終結的無意義夜晚—之時,我還是想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與此同時,我才剛起步的園藝自學也被擱在一旁。感覺是白費工夫。我們家的未來,就跟我們關係的未來一樣模糊不清,充滿變數。如果我們不得不賣掉這個家,我就不會有陽台了。沒有陽台,我也就不會有這些植物了。我無法想像在自己所布置的這塊天地以外的地方培育或欣賞它們。在這個節骨眼上還擔心香芹是否結籽,未免也太愚蠢了。雖然園藝活動已經從生活中的一種點綴,發展成生活中令我著迷的重心之一,但沒有幾件事能比得上我才剛經歷過的,那種痛徹肺腑的心碎。沒有他,我對其餘一切都失去興趣。
不過對植物來說,陽光和水依舊是十分迷人的組合。我幾週前花時間種植照料、為數不多(甚至可說頑強)的一年生植物,以及倖存下來的多年生植物,都正好達到生長巔峰。牆邊有一株開著藍紫色小花的羽扇豆幼苗兀自傲立著,周圍是假馬齒莧,它那如泡沫般的細小花瓣散發著柑橘香氣。角落裡的紫葉酢漿草已經冒出許多小巧花朵,把細小的莖壓得忍不住下垂。牽牛花和非洲雛菊則開出耀眼的粉色與紫色花朵。我走到玻璃門前,額頭靠在門上望向陽台,並未刻意鎖定哪棵植物。突然間,我感覺這層公寓好大,好安靜。如今這兒已經不會有人問我在做什麼了。努力撐著忍住淚水的壓力,以及純粹的疲憊感,就停頓在我的眉間,重壓在我的眼皮上。一股沉悶且久久不散的痛楚。我難以理解門外烏雲天正在上演的好戲,也難以理解在驟雨的對照下,植物們那明亮的色彩和旺盛的生命力。我和自己約好不哭的,卻失約了。
然而,在第四個午後,我有了新發現。我回到家,看見陽台被雨水打濕的灰色地板上出現了新訪客:兩朵飽滿、毛茸茸的罌粟花苞已經綻放,露出如同洗淨的亞麻布般鮮嫩、完美、潔白的花瓣。我倒抽了一口氣,因為它們像是挑釁似的,在那陰鬱的空間中閃爍著令人驚喜的光芒。那我熱切觀察數週(有些甚至是數月)的花苞真的綻開了,令我大吃一驚。這一切就宛如在我背過身去或分心之際悄悄發生似的。
我開始意識到,這些植物並不在乎。它們不在乎我是戀愛還是失戀了;它們不在乎我因為心碎而不再照料它們,也不在乎我之所以開始種些花花草草,只是因為想養些東西來安定心緒,來修復一些我甚至沒意識到該修復的事物。它們對我的心理狀態一無所知——它們當然不會知道,因為它們並非帶有情感的生物,至少以現今人類的理解而言是如此。而且,無論喬許和我之間發生了什麼,無論人們對彼此說了或做了些什麼,植物依舊會生長、開花、結果、死去再重生。因為它們生來就是如此。
我並未制定任何偉大的計畫,也沒有發誓要引導自己走上幸福之路。但我漸漸意識到,意料外的變化並不總是壞事。那幾朵罌粟花便是我理解的開端。儘管對植物與種植的語言一無所知,我卻發現自己正努力想理解這個語言。我想去探索每天靜靜在我們身旁開展的生存之道。當我開始嘗試去笨拙地、緩慢地解讀它,這也幫助我釐清那些發生在我身上的事;不僅僅是分手這件事本身,還有我期望能從這件事上學到什麼,以及我希望這件事會如何落幕。
*以上內容摘錄自《這一年,我靠植物找回自己——讓疲憊歸零,綠活慢療重啓人生》。本書為愛麗絲・文森著,鼎玉鉉譯,臺灣商務出版。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