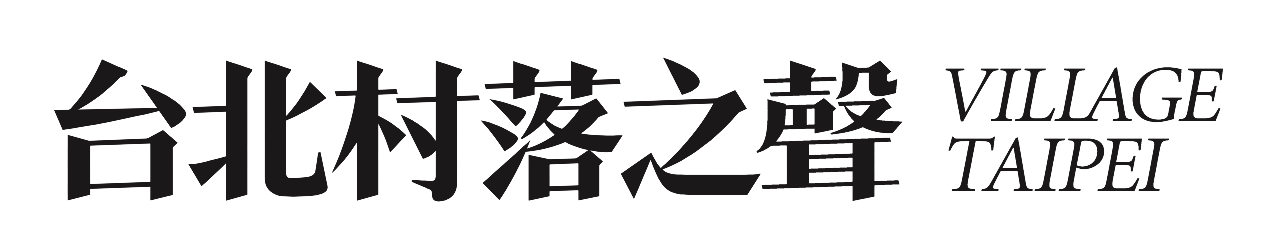
撰文/ 殷寶寧
【精選書摘分享】台北.城市.博物館
生態博物館
人類及其所生存的環境,這兩者為生態博物館定義所包含的兩大軸心概念。在此,所謂的「人類」係指稱所有民族學博物館所稱人類,也是文明社會,以及建築歷史與藝術史中所述及的人類;而生存環境可以指涉自然環境,也包含社會與文化環境。換言之,生態博物館關心的是人類及其所生存的環境(周佳樺,2014:32)。
「生態博物館」一詞的用法乃是由瓦西伯翰(Hugues de Varine-Bohan)所創發。1971年出現於格林諾伯(Grenoble)的國際博物館會議,用以界定他和法國另一位博物館學者希維耶(Georges Henri Riviére)當時在博物館界共同推動的一個運動(張譽騰,2003:14)。
希維耶很早就撰文主張,生態學概念所指涉與關切的是人與環境關係。但強調應以整合性的觀點,而不應劃分自然及人文兩個環境分類。先於生態博物館這個名詞出現的1970年代,博物館早就已經關注如何帶入自然保育的概念。但在1960年代末期的博物館,不論角色或功能因已經漸趨於老舊保守,處於社會之中,卻對社會當今的課題毫不關切等矛盾均備受爭議。而「新博物館學」在這個時間點浮現,強調博物館應該善盡為民主社會服務的功能,擔負起社會使命,創新其展示溝通方式,以及博物館跨學科領域的重要專業特色等等觀點,正是與生態博物館的概念相互呼應。
1965年,希維耶自國際博物館協會主席卸任後,即積極參與法國數個博物館計劃案,並於1967至1975年間,創立「地方園區」(parc régionaux),即現今所謂的第一代生態博物館。他本人曾指稱,「生態博物館」這個用語在法國出現雖然是新創的,但概念的根源來自於北歐的戶外博物館(周佳樺,2014:33)。
周佳樺的研究指出,隨著「生態博物館」一詞受到各方廣泛傳播,法國學者莫爾(Marc Maure)對於這個用語可能產生的混淆,特別提出解釋。在他的說明中,「生態博物館在法國以兩種不同方式定義,當指涉『園區式生態博物館』(l’écomusée de parc)時,定義採希維耶者;當指涉『社區式生態博物館』(l’écomusée Communautaire)時,則採瓦西者。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分別,不僅攸關反映法國70年代的實際現況,也為國際上對這詞使用的兩種型態之理解,有所助益。」(Maure, 2002:188,轉引自周佳樺,2014:36)
在此,所謂的「園區式生態博物館」,比較接近前述提到的北歐戶外博物館模式,所謂的「戶外」是指座落於室外,通常是自然園區的形式,但博物館本身的館藏,則是屬於民族誌性質。隨著時間演進,到了1970年代後,所謂的生態博物館概念,「戶外」這樣的形式仍然保存,但未必是座落於自然景觀園區,而可能是一座工業遺產城鎮,或是一座歷史城市等等,而在此,所謂第二代的生態博物館的概念,「民族誌」的色彩已經淡去,或甚至不存在了。這也就是所謂的「社區式生態博物館」,回歸到從人與環境的向度來詮釋。如此一來,對於人類遺產的詮釋,可以隨之擴大,而戶外博物館的型態也就不限於北歐的民族誌性質的模式了(周佳樺,2014:34)。
綜合前述北歐、德國和法國生態博物館三個案例模式。法國對於文化事務的推動是較為中央集權的;相較而言,德國發展出為數眾多的地方博物館,凸顯各個地方在地歷史地理的文化差異。至於北歐,因其傳統上非常重視鄉村文化,以傳統風土建築、農村景觀,動植物保育等模式發展出來的戶外博物館,展現且貫徹其對於民族誌/民俗傳統的保育意圖。換言之,從保存在地與民族傳統、知識、情感與集體記憶的目的出發,這三個地區所發展出來的博物館類型不盡相同,北歐以戶外博物館的型態來展現;德國納粹時期發展出來的地方博物館,之後也跟上北歐的腳步,出現許多戶外博物館(楊凱成,2021);而法國則進一步地將這樣的發展軌跡,具體以「生態博物館」的用語來指涉。只是,隨著時代演進,特別是「生態博物館」一詞因為兩位主要的傳播者,前後都曾出任國際博物館協會的主席,讓這些概念更廣被傳播、討論及活用,並且從最初的特定範圍、園區式的戶外博物館,逐漸拓展到社區概念的生態博物館,也使得人與環境中所蘊涵的「遺產」,可以循著這樣的知識與思考脈絡,被更為周詳地納入生態博物館的保育範疇中。
前述這些概念與發展軌跡,延伸到本文所關切的城市博物館概念。可以再整理出幾個重要的思考軸線。
首先,前述的幾種不同範疇的博物館類型討論,共同的焦點在於對在地歷史、文化、情感與集體記憶的關注。但表現形式,北歐式的戶外博物館以傳統的建築、空間環境、動植物與生活軌跡的保存,作為一種民族誌博物館的形式,聚焦於「民族」的分類概念。德國的地方博物館模式則同時含括了特定的在地地理區分,與在地族群這兩個分類範疇。共同指涉了社群/民族/國族等具有同質性的群體關係。
然而,「城市」這個概念則是以地理範疇為邊界,而在城市中涵納的人們,基本上是多元混雜的,不以共同的民族/國族分類作為歸類或服務的對象。甚至,在城市文化的推展中,是高舉且讚頌城市居民組成的多樣性繽紛,為城市的優勢與特色所在。
其次,前述以民族誌為隱含假設的博物館分類範疇中,在地的地域界限與族群分類,有著其涇渭分明、可茲分辨的界線,不論是地理的,或是人群的,並以此作為蒐藏物質文明的論據基礎。然而,在城市博物館的討論中,則是將「城市」本體視為人類社會發明的「人造物」,這個「人造物」本身即為物質文明的重要本體與載體,是城市博物館所欲探索、研究、典藏與展示所在。這樣的特徵也迥異於其他類型的博物館。
第三,由於「城市博物館」與城市是一組共生的複合體。城市必然有其行政管理的政權實體,這個權力主體如何理解與詮釋自身,反映在城市博物館的經營與運作過程中。
第四,城市是不斷向前與時間並進的。換言之,城市的變遷與行進路徑影響著城市居民的生活,城市博物館也與這樣的未來性緊密相依。
帶著這些前人所提供的豐富知識資產,城市博物館的探索之旅,繼續前行。

*以上內容摘錄自《台北.城市.博物館》,殷寶寧 著,大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